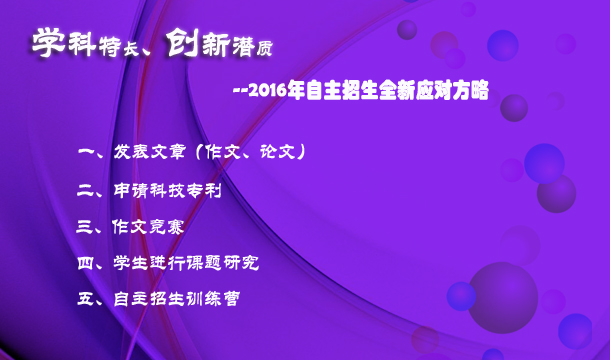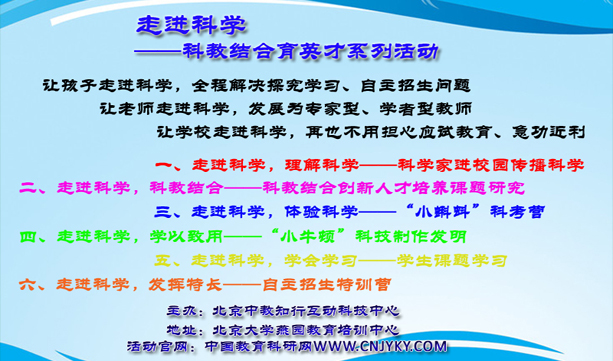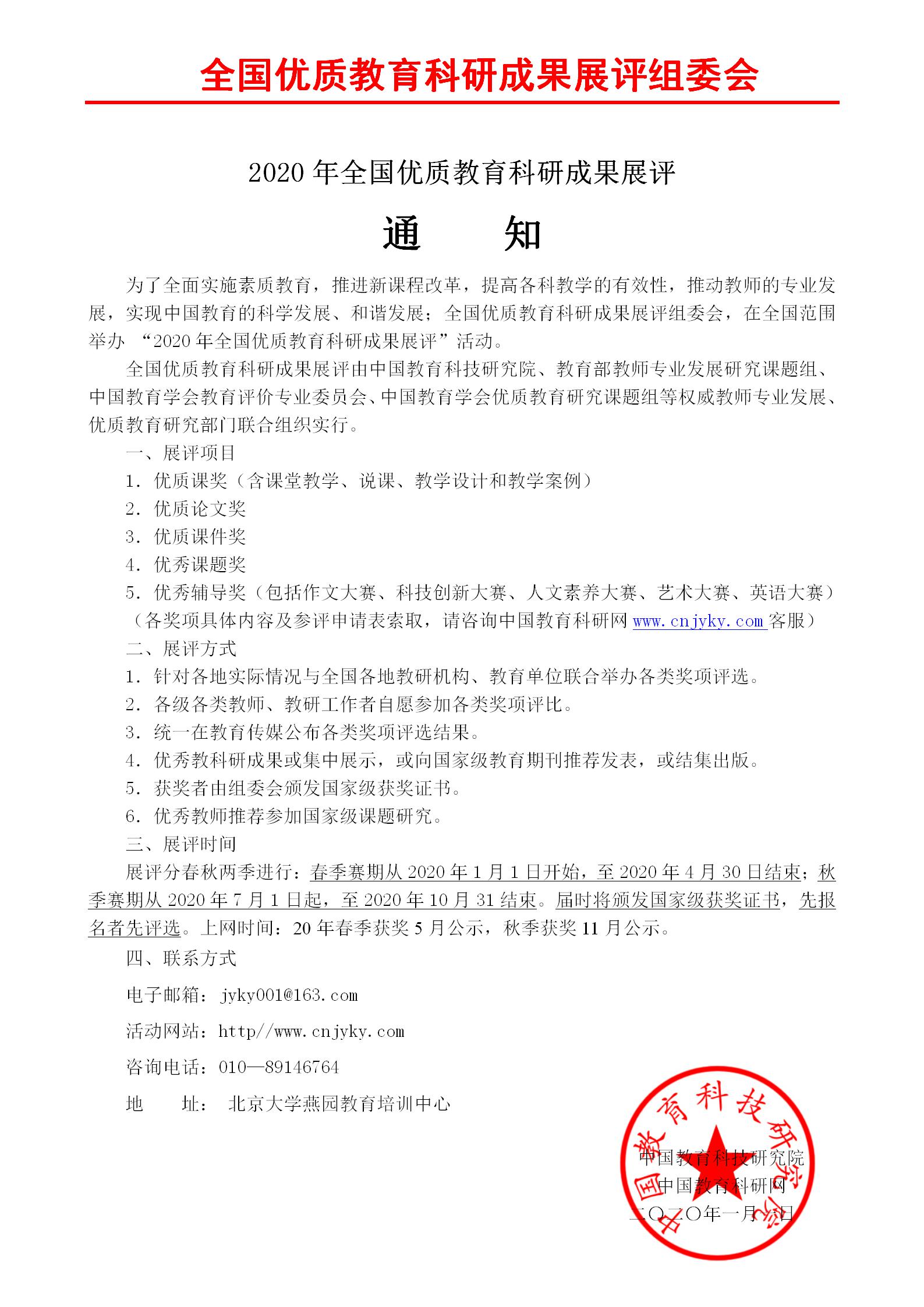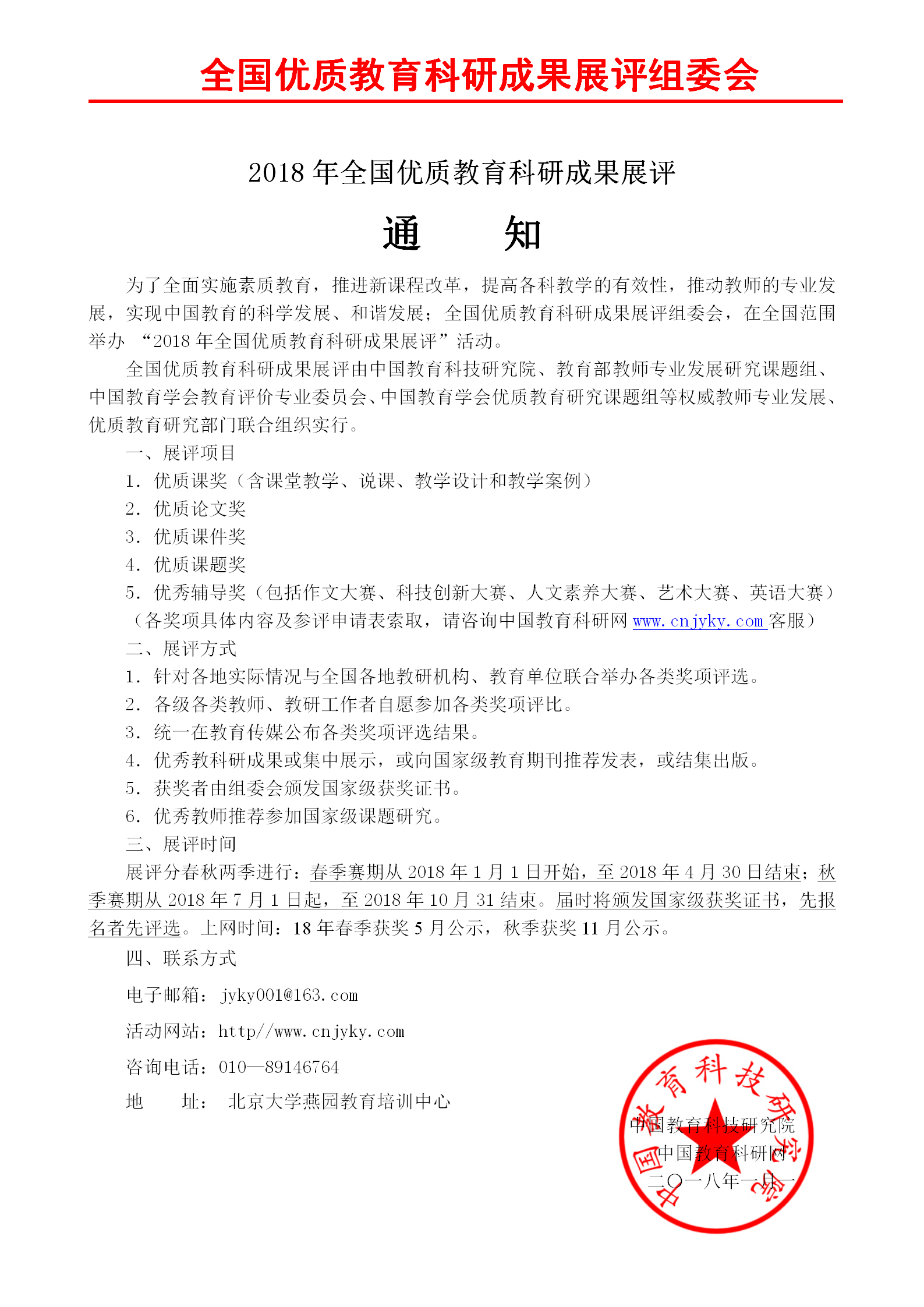| 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科学 |
| 时间:2015-05-07 来源:吴国盛 |
|
科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它在一个文化传统之中孕育、发展,与这个传统之中的其它亚文化发生相互作用,受制、受限于这个传统为它所预设的发展空间。这是近百年来,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所得到的一个比较公认的结论。如果同意这个结论,那么我们比较习惯接受的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就需要反省。所谓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就是认为全人类只有一种科学,或者说,严格意义上讲只有一种科学,也就是标准科学,除了标准科学之外的所有自然知识形态,都只是或远或近的接近这个标准科学。这个接近的程度,就是评价这些知识形态是否科学的标准。通常,那种唯一的标准的科学,也就是在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 与普遍主义的科学观相联系的是对科学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把科学看成是一种与办事情的“有效”和“效率”相关联的方法、方案,而不是从人类的存在方式角度来理解科学,因而更多的从“用”的层面来理解科学。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把科学看成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我们才能够理解文化传统与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不同的文化传统,就会有不同的科学。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种文化,这些文化各自都有自己的科学形式。然而,正如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在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样,也不是所有的科学形式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在本文中准备讲述的三种有突出的历史地位的科学,这就是希腊理性科学、近代西方的数理实验科学以及博物学。在给出三种科学的论述框架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的影响问题。希腊理性科学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认同,从希腊理性科学到近代欧洲的数理实验科学的发展,构成了“科学”的正宗来源。即使没有把我们中国看成是科学的发源地,我们似乎也可以承认这一点,因为对现代中国人而言,“科学”这个词确实是一个外来词,我们的古汉语里面没有科学这个词,它是英文science的一个翻译,而且还是日本人翻译的。日本人觉得西方人的这个学问,science,跟我们中国儒家的学问不大一样,儒学是综合性的学问,文史哲不分,而这个science是一个分科性的学问,数、理、化、天、地、生,所以把它翻译成“科学”,取分科之学的意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就“科学”进行追根究底,首先要承认它是一个洋学问,来自于西方。此外,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所谓科学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以数理实验科学为主体的科学的时代,所以我们谈科学从希腊开始谈起是有根据的。 希腊人的理性科学与希腊的人文理念有关。我在别处多次讲过,不同的人文理念伴随着不同的人文形式,“理性科学”在希腊时代,作为一种人文形式,是与希腊人对于“自由”的追求,与他们把“自由”为作基本的人文理念密切相关的。比较起来,我们中国古代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文理念,因而也伴随着不同的人文形式。我的意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是把“仁”作为基本的理想人性,而把“礼”作为达成这种理想人性的基本形式。 过去许多人总是疑惑,说我们中国人也不笨,都很聪明,为什么我们古代就没有出现西方历史上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呢?我想我们不应该从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只能说不同的人文追求,决定了一个民族会把他们的主要精力和智力运用到不同的领域。我们中国的人文形式,并没有体现在科学方面,而是体现在我们的文学、艺术、礼仪、道德方面。 希腊人不同,他的最高人文理念是自由。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自由的话,那么他就只能是奴隶,就不可能成为希腊世界中高贵的人。那么怎么样才能使他懂得“自由”呢?希腊人认为只有学习一门叫做“科学”的知识,才能进入自由的境界。而科学,在他们看来也就是所谓自由的学问。所以希腊科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纯粹的非功利的。希腊科学的第一个形态是数学,数学也是希腊时期最发达的一门学问。数学按我们今天的看法,应该属于理科学问,可是在希腊时期,它恐怕得算德育课程、政治课。因为在希腊人看来,唯有通过数学的方式,我们才可以领悟到那个最高的人文理念“自由”。数学的对象是很奇特的,几何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圆,我们现实中的圆没有一个是真正圆的,我们看到的圆或多或少总有点不圆,只有几何学中的圆是真正的圆,是一个最完美的圆。因此,希腊人认为,我们唯有通过学数学才能知道有一个理念世界存在,它超越于我们的此岸世界,这个世界中的所有成员都是最完善最真实的。希腊人由于发现了这样一个超越的理念世界,而创造了一门理性科学。 理念世界与理性科学的一个特征是纯粹性、内在性。如果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精神世界永远纠缠在各种各样的现实纠纷之中的话,那么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是纯粹的,我们就要考虑各种各样的现实因素,我们也就不可能给出一个纯粹理性的方案来解决我们世界的问题。比如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更多的是随机应变,见机行事,原则性不强,总是可以通融,这确实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文明道路。希腊人认为,那个最真实的世界是纯粹的,是绝对的,因而是内在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知识,就是哲学。这里所说的哲学,其实也是理性科学的一种形态,是成熟得最早的一种典型的科学形态。严格讲来,中国古代既没有现代数理实验意义上的科学,也没有希腊理性科学意义上的哲学。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说,一个没有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句话反映了希腊人的人文追求。在他们看来,一种生活的理想是通过批判方式而获得的,它不是通过祖宗传下来的,不是通过某种宗教信条灌输下来的,而是通过理性的考察,理性的论证才获得的。内在性、纯粹性和批判性是希腊理性科学的基本特征。 这样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自由的追求,这样一种精神,并不是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有的。现代思想家普遍意识到,近代欧洲的科学之所以能够出现,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吸收和综合了希腊的科学精神有关系。 近代数理实验科学 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也有全新的东西出来。这与近代西方的文化理念有关。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代表了近代西方科学的源头处的精神,一个是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一个是法国的笛卡尔。培根有一句名言叫做“知识就是力量”,他强调近代科学必须用来增进人类的物质财富。培根科学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科学形象,就是力量型的科学。科学技术必须转化为生产力,必须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力量。 近代科学的另一个方面可以由笛卡尔来标志,他也有一句名言,叫做“我思固我在”。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比较深奥,但却指出了近代人的精神世界所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型。首先,它表明了现代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时代。再者,“思”表达了对希腊理性科学的一种继承。笛卡尔像希腊人一样认为,我们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的世界,是一个内在的世界。只不过,这个世界过去不由人所掌控,是一个超越的神的领域,现在,开始回归到“我”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今天的价值原点,今天的精神支柱,开始奠定在大写的我、大写的人类主体之上。笛卡尔指出了现代人类精神的基本动机是主体的“思”,主体的理性诉求。结合培根对力量的追求,就形成了近代精神的本质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will to power,强力意志,或者求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求力意志构成了近代主体性的主要内容,也构成近代文明的主旋律。 近代科学一开始,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有所作为。所以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是我们新科学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使命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型的科学必须是力量化的。这种力量化的、主体外化的新型科学的范式体现在很多方面:第一个,现代科学允诺了一个无限的世界图景。其次,允诺了一个无限上升的、进步的历史演化图景。第三个方面,自然被看作一部数学的机器,看作一部可以计算、可以量化的机器,这成为近代科学的另外一个形而上学基础。近代科学为了达成自己控制和征服的目标,它需要创建一个控制论的模型。这个模型基于一种新的因果概念,即刺激-反应型的因果概念。原因作为一种范畴在希腊时期有四种,有目的因、质料因、形式因和动力因,到了近代以后,四因只剩下一个因,就是动力因。这是因为控制论思想在作怪,对自然的控制、征服和改造成了一个主导动机,于是自然知识体系只抓住了也只需要抓住动力因的方面。所以说近代的数理实验科学本质上是控制论的、机械决定论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掌握不同的输入会导致什么的输出,从而完成对自然系统甚至社会系统的控制。控制的、支配的动机,要求数学化、还原论的纲领,这是近代的数理实验型科学的基本特征。 近代科学经过20世纪的发展,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然界本身未必是一个机械论的体系,我们的生命系统未必是可以完全还原的,所以20世纪兴起的很多新的学科,比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非线性科学、混沌学和生态科学等等,越来越展示了一个和古典科学不相同的世界图景。人们发现,世界本质上可能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完全可控制的。 在过去的两百年内,近代科学及其技术,是产生了非常伟大的成就,它确实从总体上,把人类这个物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人类的主体意志。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看就发现,近代的以控制论为主导的这个科技体系难以逃避两个界限。第一个界限就是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规定的熵增现象。一切机械体系都必定向外界排出高熵,我们的物理体系很难避免熵增的后果,并且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越厉害、越是追求和制造新的秩序,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向外界输出的熵就越多,这是宇宙论和物理学上的一个限制。第二个界限就是自然系统的不确定性。过去我们总是觉得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决定论的,我们原则上可以预言自然界的未来反应,原则上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但是现在来看并不一定。 博物科学 作为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及其限度的反省,我愿意提出博物科学的复兴方案以供讨论。博物学是最原始的科学形态,也是多样化的。所有的古老文明、所有的原始文化都有博物科学,都有对居住地周边生态环境和动植物的一个基本认识,对周围的地质地貌特征的基本认识,这样的认识符合原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是一种基本的、内在的生存知识、生活知识。 为了克服今天这个单纯的征服型的、力量型的科学的局限,我提出两条路线。第一条就是要重新唤醒对希腊理性科学的重视,从西方科学的源头处,找到克服近代力量型科学的限度的根据。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弘扬科学精神的真正动因,也就是说,弘扬科学精神就是要重温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我认为,希腊人开创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就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这条线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还不是特别熟悉,也不大容易为中国学界所理解,因为我们中国不是近代科学的故乡,也不是科学精神的故乡,希腊人那种对自由,对理性,对真理的单纯的追求,对古代中国人来讲是闻所未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许多西方的文化精神,都不大容易引进。比如我们能够接受“法制”但不太接受“法治”,前者说的是使用法律这种方式来治理国家,后者则说的是按照法律的要求来治理国家,前者法律是工具,后者法律则是最高的准则。科学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接受科学作为工具,却不容易接受“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为科学而科学”这种自由的精神。这条重温希腊自由精神的线索,还需要下大力气才有可能收到效果。 第二条路线就是博物科学的复兴。博物学英文是natural history,直译是“自然史”,是对大千世界丰富多样的自然现象进行收集、分类、整理的知识,在早期,它实际上差不多涵盖了除数理科学之外的所有自然科学。像法国18世纪的博物学家布丰的44卷本《博物学》,不仅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的知识,也包括天文知识、物理学知识,属于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个百科全书式的风格正是博物学特有的风格,我们中文称为“博物学”也含有博学的意思在里面。 博物学在近代以后慢慢的丧失了它的地位,因为在生命科学领域里,那种单纯的收集和发现生物多样性,以及对它们进行分类、研究它们的亲缘关系这样的学问,渐渐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对自然界隐藏着的决定论的“规律”没有足够的洞察,因而在近代征服自然的时代主题面前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生物学的其它分支,就是那些按照数理实验传统的方法对生命世界进行研究的新兴学科,慢慢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今天我们一提到生命科学,就想到了实验室,想到了分子生物学。越来越多的大学不再开设博物学的课程,认为这是小儿科,是哄小孩子玩的,是非常初级和低级的学问。 我认为,博物科学的意义恰恰不能从单纯的有用性,单纯地控制和改造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它代表的是与近代西方数理实验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科学传统,它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与近代数理实验科学完全不同。恢复博物学传统,目的在于改变现代主流科学对待自然的态度。 博物学首先一个特点是要聆听自然、倾听自然,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态度,对自然保持一种谦恭的态度,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自然,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不是实验室中遭到“拷打”和“拷问”的自然。实验室的基本方法就是把事物切开来、分解开来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背后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知道了局部就知道了全体,窥一斑而知全豹。所以实验室科学的有效性,建立在这个世界的普遍统一性之上,建立在时间和空间的均匀性之上。但是我们知道博物科学不需要这个前提,它并不要求一种普遍的有效性,它所要求的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直接的接近,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博物学改变的是科学对待研究对象的一种心态。博物学的对象不是无情的,而是有情的,博物学家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要付诸情感的。所有的博物学家都对事物本身有一种热爱,有一种同情和了解。近代科学主流从某种意义上培养了一种人对于自然的“自豪感”或者叫“傲慢感”,那是一种因为拥有科学知识而产生的对于自然的傲慢,以及对于其它物种的“优越感”,缺乏对其它事物的“同情”,没有一颗同情之心。总体上讲,近代主流科学事实上培养了一种对于自然万物的“无情”之心。近代的数理科学就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处,就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冷冰冰的,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个数学体系,是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一个体系。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一个要求就是把科学家的个人的追求、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情绪排斥在科学研究之外,通过这样一个去人化的过程,来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要求对实验科学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的目标是达到一种有效的控制,如果你加进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因素,当然难以保证它的高效性。与数理实验科学传统相反,博物学要求一种对自然的亲近,对自然的情感。 博物学的复兴根据何在?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有现实的根据。我认为,现代的许多新学科,特别是以混沌学、非线性科学和生态科学为代表的新型学科,实际上是在复兴某种博物学传统。博物学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并且以捍卫这个多样性为自己的使命,决不会以追究现象背后的数学结构来消灭多样性。从博物学角度看,多样性乃是我们一切知识的源泉,也是我们生活意义的来源。维护自然生态其实也包含着对文化生态的维护。 今天我们一提到“科学”二字,大概指的都是近代的数理实验型科学,是功利性的、力量型的、征服和控制型的科学,而沉思型的理性科学和亲近自然的博物科学,不大被人重视。但是我们可以讲,希腊的理性科学是近代数理科学之根,博物学则是近代实验科学之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传统的根在两千年前的希腊,更在更加久远的古代。应该说,希腊的理性科学是我们中国文化所不熟悉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为学问而学问,为追求自由而追求真理这样的科学精神,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纠偏现代科技,我们中国文化是插不上嘴的。但是,从另外一条路线,即从博物型科学角度去纠偏现代科技,却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说上的话,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博大精深的博物学资源,我们的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我们的中医药学,都是非常好的博物科学。我们的天人合一的智慧为今天对生物多样性的追求和环境保护的思想,提供了精神资源。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博物学,实际上是要激活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的这个因素,来纠正或者克服当代主流科学中出现的某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 在讨论了三种科学类型之后,我们再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呈现出三种可能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科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近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未来科技。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科技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它们相辅相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近现代的科技之间则相反,实际上呈现出相互排斥的局面,原因是,中国近现代科技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土科技,而是来自西方的近代数理实验科学,这种数理实验科学所要求的近代西方的人文理念以及它所传承的希腊理性科学的理念,均与中国传统文化大相径庭。至于未来的科技,在克服和纠正目前西方的数理实验科学的局限意义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的,但是否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则不能断言。 |